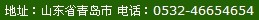|
拓荒与殉道—我的文学心灵史 作者:陈新元 我喜欢高尔基的名言:人在本质上是个大殉道者。他说的道是信仰,而我理解为文化。人是一种文化熏陶的产物。我十六岁成为兵团无数拓荒者队伍中的一员,六十岁有了散文集《走过喀什》、纪实文学《大漠足音》《拓荒者》等著作,成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兵团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现在仍在笔耕不辍,文化的源泉尚未枯竭。没有在拜佛磕长头的人群里,没有在西去朝觐者的颠簸途中,在拓荒者的队伍里我成为一个大殉道者。是新疆兵团的丰厚的文化土壤滋养了我。兵团文化有看得见的:电影、广播、文艺团体、文学刊物等,也有看不见的:人与人之伦理道德情操、理想追求、“大家庭”的互相熏陶等。我讲的主要是后者。 大漠中的文学雨露我初中毕业品学兼优,却因父亲冤案株连被剥夺了升学的权利,在农一师前进二场(今第三师四十二团)当了农工。一年后,调到农场测量组当测工。“文革”狂飚突起,除了“毛选”,无书可读;除了“语录歌”,无乐可听。我们的帐篷支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缘的荒漠里,沙浪像凝固的大海。我们不但生活在大自然的沙漠里,而且精神世界一片寂莫空虚。幸亏我遇上了一位影响了我一生的好班长。班长姓孙,名祜,四川人。解放战争三年,他在国军中干了一年半,在解放军中干了一年半。我们常笑他“半个国军半个共军”。他家资颇丰,上过初中。他酷爱两样东西:《三国演义》和酒。这两样爱好深深影响了我的人生道路。那年月《三国演义》被批为“四旧”,而在荒无人烟的大漠里,班长照讲不误。他重现了四川说书人的神韵,川音抑扬顿挫,细节刻画生动,如见其人,如临其境。听得我们三个年轻人如醉如痴。他说起酒更是听者痴,说者醉。那年冬天,我们在大漠里测地形图。中午,点堆火烤热苞谷馍,吃饱往沙包坡上一躺,眯着眼享受阳光。班长卷了支莫合烟吸一口,长叹一声“有口酒喝就安逸了!”官儿小,娃儿多,哪有酒喝!环望长天大漠,老班长忘情地吟道:“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我被这精美绝伦的吟酒诗强烈震撼了:“太好了!”边说边用红柳枝把诗写在沙滩上。老班长脸笑成了核桃皮,朗声背诵《将进酒》“……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大漠中飘洒着看不见的雨露,我年轻的心田被播下了一颗奇怪的种子,特别喜欢听老班长背诵古诗,听他说酒。西方哲人说,文学是魔鬼的药酒。我年轻的心灵那么肥沃那么神奇,种什么长什么。魔鬼的药酒悄悄发酵了。我开始喜欢文学,自学古典文学。父亲悄悄把“文革”风暴中幸存的《唐诗三百首》交给我。可惜被喜欢李白的老鼠啃去了七八十首。我如饥似渴地读着,时常在戈壁滩上背诵诗歌给组长听。我们心拉近了,他给我掏出心里话常常使我震惊:那年团场征兵,我积极报名甚至写好与家庭“决裂”的决心书。结果被冷峻拒绝。走在荒漠里我一脸沮丧,万念俱灰。老班长却轻飘飘一句话:那些招兵的人没有打过仗,不知道打仗是要死人的。如果真的打起仗来死的都是贫下中农,活着的都是地富反坏右;招兵的人不后悔死了啊!我一愣,一下子沮丧全没啦!还是活着好!还有一次我们去团部看到造反派在练习刺杀,自制钢筋长矛一片喊杀。我浑身惊颤,老班长只是轻蔑一瞥。走到沙丘上,他边卷莫合烟边说,革命在倒退,你看他们手中的武器就知道了。大革命时农民赤卫队用大刀长矛,红军时有老套统,机关枪;抗战时有三八式迫击炮;解放战争我们交给解放军是美式武器啊!你看,他们今天又拿起长矛岂不是倒退!我一下子转不过弯子强辩说,前进倒退要看路线啊!老班长一笑说,路线是理论是脑袋瓜子里的东西,你要看他的手在干什么。路线?你看,红军的手对国民党的士兵不侮辱人格不搜腰包,伤兵还给救治。现在,他们的手在干啥?给人戴高帽子游街,拳打脚踢,八叉都画到脸上啦!不是倒退?老班长把人的良知搀和到魔鬼的药酒中,我浑然不觉走上了文学那条被看作“异己”的路。奇怪,荒原中处处有“魔鬼的药酒”!我遇到一位资本家出身的上海青年,外号“顾大个子”,英俊潇洒,根本没有出身不好“夹着尾巴做人”的假象,说话风趣幽默。他在上海报名时,慷慨陈词:“不吃定息吃新疆包谷馕,好儿男志在四方”。招兵工作组被他高大英俊雄辩滔滔感动了,立即决定批准他进疆,但先留在工作组帮助做动员工作。他说“我动员的出身不好的进疆青年可以拉好几个火车皮!”为此,他到了团场光荣地被批准当了推土机手。那时拖拉机手要查祖宗三代贫下中农。在荒原上修渠工地,每逢他上夜班我就跟着去。在余温未消的沙滩上,在繁星密布的夜空下,他讲莫泊桑的《羊脂球》,都德的《最后一课》,甚至讲一段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中艾德蒙·邓提斯掉包越狱的故事。这些故事深深震撼了我,我第一次感觉到西方不仅有“万恶的资本家”而且有和我们一样的有气节有感情有良知的人!非常奇怪,在远离“革命洪流”的大漠拓荒者人群中,我睁开了第三只眼对社会看得越来越清晰了。“自流人员”悄悄告诉我饿死人的真相;挑担送水的“劳改犯”低声说,抗战主要是国民党军打的,少将以上战死二百多个;子弟兵老战士说到“肃反”黯然伤神;我的心一次次震动颤抖······粉碎“四人帮”后,我如饥似渴跑到喀什新华书店把顾大个子讲过的那些书全部买来,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啃起来。而且,我也变得喜欢给别人讲故事,无意识地泼洒“魔鬼的药酒”。 我与维吾尔文化新疆的汉族文化人如果不了解维吾尔文化,不是完整的高水平的文化人。写新疆的文学作品如果仅仅反映这里的汉族生活,没有多民族文化因素,无论如何是个缺憾。我出生在伽师县,从小在部队,兵团长大。与维吾尔人的接触是间接的肤浅的。年冬,自治区革委会决定把图木舒克垦区划归兵团农三师,包括原属农垦厅的巴楚总场和两个人民公社。我被抽调到工宣队,与维吾尔人生活了一年,近距离接触了维吾尔文化。我遇到了一位刚从中央民族学院维语系毕业分配到兵团接受“再教育”的汉族青年,拜他为师,刻苦学维文。我口语基础好,学文字很快。一年时间我学完了大学维语系一年半的教程。仅仅在维吾尔文化的大海边掬了一捧水,就是我兴奋了迷醉了。这个民族的形象思维非常发达,酷爱富于想象力的浪漫的诗歌哲言,具有活泼快乐热情直爽的天性。比如成语翻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译为“趁你牙齿好,赶紧多吃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译为“刀子插在自己身上不觉得痛,才能插向别人”;告诫恶语谎言:“谁往天上吐痰,掉下来就会落在自己脸上”;告诫狂妄自大:“豌豆跳得再高也砸不烂铜锅”等等。我常常与维吾尔干部坐马车聊天,他们极少讲“阶级斗争”“忆苦思甜”等,讲得最多的是阿凡提的故事,风趣幽默,生动鲜活。对“文革”的说法更有意思,那时粮食定量低,几乎没有肉油,生活贫困。维吾尔干部说,现在生活好得很,粮食吃不完都贴到墙上去了。饿了扒下来吃就行了。他说的是大字报。我收集了不少维吾尔谚语;故事;传说。其中一个:在胡杨林深处有一座“四十姑娘坟”,维语“克热克克孜麻扎”。相传古代(伊斯兰教传入前)一个北方部落侵占此地,奴役刀郎人。刀郎人奋起反抗,寡不敌众,被围困于胡杨林深处。北方部落提出献出四十个姑娘就可以网开一面,给条生路。为救刀郎部落,四十个姑娘挺身而出,来到北方部落首领大帐前。刀郎部落立即突围而走。四十个姑娘拔出暗藏利刃从容自刎。北方部落首领惊骇万分,下令不可追杀,刀郎人不可战胜。遂退出图木舒克。千百年来,刀郎人代代相传“四十姑娘坟”的故事,子子孙孙祭奠“四十姑娘坟”,从未间断。今天,“四十姑娘坟”已成为旅游景点。这里的人们讲到这个故事都会自豪地说,我们是刀郎人的后代。从图木舒克工宣队会四十二团后,我因为会维文被调到团部中学当初中班主任,兼教高中维语课。班里有一位维吾尔女学生吐莎汗,汉语流利,温和听话。有一次初冬种树挖坑,被一个汉族女同学坎土曼砍伤头部。我医院包扎。医生说幸亏她头上有铁发卡,没有危险,观察一两天就可以出院了。我一夜未眠,想着怎么去她家里解释这件事。如果这事往“民族问题”上一扯那就麻烦多了。班主任必须承担一切责任。我想了一肚子自责的话。没有想到第二天去了她家这些话一句也没有用上,倒是她父亲阿里木江深深感动了我。原来,我当了这个班主任后,吐莎汗回家告诉了父亲。农场人长期生活在“大家庭”,互相知根知底。阿里木江很快知道我是“李班长的儿子”。我母亲从解放初就是部队被服厂的裁缝,在团商店缝纫班人称“李班长”。母亲为人善良,有口皆碑。对孩子多,家庭困难的职工不论汉族维族,想尽办法补衣服,不要钱或者尽可能少要钱。我进了吐莎汗家一见阿里木江,他说,我们的衣服是李班长做的,补丁是李班长补的;我们几个孩子哪个身上没有李班长的尺子针线?我们不会给李班长的儿子找麻烦。再说那个汉族女同学也不是故意的······在我的记忆里,这是第一次被维吾尔兄弟感动得流了热泪。我把这种感情融入了散文,我把维吾尔文化的形象思维融入写作。有的年轻人看了《走过喀什》《拓荒者》,问我写作秘诀。我说你写东西时记住,把政治还给政治家,把哲学还给哲学家,文学是人学;你就写人的感情或者说带着深厚的感情写人,就算入门了,没有“秘诀”。要说有,那只能是真善美!感情是不能用来讨巧的,那是长期积累深入体验的结果,《文心雕龙》里专门讲了“情采”。 余秋雨和陆天明年兵团恢复后,我到农三师宣传处工作。先是新闻干事,后是副处长,文联主席。我自学了高中文科学业,考上新疆电大中文系,取得了毕业证。师机关的文化氛围很浓,有专业文工团。师部常举办歌咏比赛,社火灯会等。因为工作关系,我接待了一个个文化大师。年金秋,著名文化大师余秋雨到喀什游览。短短两天,获益非浅。余教授为人谦和,学识渊博。他第一次到喀什一切都新鲜,总是刨根问底,凝神深思。在香妃墓,讲了香妃故事后,他问琉璃砖上的花纹象征什磨,为什么崇拜新月;在大巴扎,他问维吾尔“古丽”为什么描眉,男女花帽花纹有啥不同,当我把一句句维语翻译给他听时,他眼神很欣赏还有点好奇。他委婉地问,喀什除了“三个麻扎一个巴扎”还有什么?我立刻领他到沙俄,英国领事馆原址,清代徕宁城遗址。在残破的城门洞前,我讲了湖南士兵黄定湘为保卫这座西域名城英勇牺牲的故事,讲了后人为纪念他在南疆多处修建了“方神庙”。也许我讲得太投入太激动,他只是对我频频点头什磨也没说。在飞机场送别时,余教授郑重叮嘱说,两天时间你讲的所有故事都很有价值,你把你讲的喀什民俗,历史,风土人情等原汁原味写出来,就是一本很好的散文集。就叫《西域第一城》吧。大师的鼓励对我击一重锤!我常常白天忙着工作,夜里伏案疾书。我学过维文,维语基本流畅。我的两任直接领导都是精通汉文化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他们对我了解维吾尔人的习俗历史文化给了很多帮助。后来,我的散文集《走过喀什》出版。兵团著名的老评论家孟丁山写了序言,给予高度评价。现在网上,这些文章点击率仍然较高。 接着是著名作家陆天明到喀什采风。我给陆老师当导游。香妃墓,大巴扎,艾提尕大清真寺,转悠一天。接着去麦盖提垦区和小海子垦区。我读过陆老师的作品《泥日》《桑那高地的太阳》等,很钦佩他的才学。在我读过的所有写新疆兵团题材的作品中,他的作品最深刻最准确也最耐读。他是上海支边青年,曾在农七师工作十二年,熟悉新疆兵团生活。第一次来喀什,正好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热播他的大作《苍天在上》。中国老百姓对腐败深恶痛绝,这部电视片为民鼓与呼,深受欢迎。从喀什市、麦盖提垦区到小海子垦区,只要我一开口介绍这位是著名作家、《苍天在上》的编剧陆天明老师,立即有许多素不相识的人目光惊喜抢上一步伸出热情的手。他十分谦和地与团领导、支边青年、老职工还有招待所服务员握手,毫无骄矜之色。他像海绵吸水一样不知疲倦地倾听各种人的倾诉,记录一个个故事。特别是在一千多公里的三天路途中,车上除了司机就我们俩。一路上我滔滔不绝讲述亲身经历,他问什么我讲什么,毫无顾忌,漫无边际。文革、动乱、支边青年、兵团农场各色人等,讲的全是我的故事和心理感受。讲到我年轻时多么嘴馋,从上海支边青年那里第一次吃到华夫饼干牛轧糖,从北京青年那里第一次知道世上有种美味叫烤鸭;甚至讲了年轻的我如何暗恋女支边青年,结果是剃头匠的挑子一头热,总是被女青年用上海话说“拐特”(甩掉)。年轻司机听得不停地笑,而陆老师只是静听沉思,纹丝不动,偶尔一个微笑,问一两个细节。一路颠簸,毫不寂寞。在皮恰克村,我陪陆老师到几户维吾尔老乡家。我当翻译,陆老师专注地望着维吾尔老乡的表情,似乎担心他们听不懂我的维语,或者担心我的翻译不准确。看到老乡脸上的神情,陆老师十分满意了。在车上淡淡一句,你真不容易。相聚四天,我把陆老师送到阿克苏农一师文联。握别之后,再未见面。大约七八天后,我接到兵团文联一位领导电话,先是表扬农三师对陆老师的接待热情周到,接着郑重其事地问你给陆老师说了些什么?他在兵团领导出席的座谈会上“七八次提到你,说你最有可能写出深刻反映新疆兵团南疆生活的作品来”。我愣怔片刻,答一路上讲了我个人的经历,琐碎杂乱,不成文章,不能登大雅之堂。放下电话,久久呆立。这个信息强烈震撼了我!我真的“最有可能写出深刻反映南疆生活的作品来”?我的曲折坎坷的经历真的是阿里巴巴的宝藏?为什么在一起时陆老师对我一句鼓励的话都没说? 这个信息强烈激活了我久久深藏的文学灵感。仿佛一声“芝麻,开门”,我的经历的宝藏被打开了,我的处于冬眠状态的文学灵感被激活了。年我调到乌鲁木齐兵团纪委。一年后,我主动要求调到兵团史志办。有朋友提醒我“纪委进步快,史志办太冷僻”,我说我这一辈子人生经验是:不凑热闹,善走冷门;我是来自拓荒者队伍中的殉道者。到了兵团机关,我离兵团著名的文学杂志《绿洲》近了。我写个人经历的纪实文学《我的连队》、《我的班长》等,相继成稿。《绿洲》杂志主编钱明辉慧眼独具,发一篇又一篇,发一稿鼓励一番:“大胆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愁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我最看重的也是我年轻时血与火的经历《我的一九六九》,没有一家刊物能予发表。我决定出一部纪实文学《大漠足音》,把那些刊物不宜发表的作品收进去。新疆大学出版社领导、清史专家周轩,富有经验的年轻编辑赵星华,为《大漠足音》倾注了宝贵心血,许多涉及“敏感问题”的精彩情节,由于他们的智慧和努力才得以保留。《大漠足音》出版后引起的各种反响出乎我的意料。著名诗人李东海写了热情洋溢的评论;石河子大学文联刘主席说,你的书反映的兵团南疆农场基层生活最真实最生动;书中涉及的许多人纷纷来信来电话,谈感想,诉衷情,热情鼓励;《我的班长》孙祜的女儿说,我们边读边掉泪,你对我父亲的了解超过了我们!喀什作家马树康,把《我的一九六九》的史料部分编入《喀什文史资料》。一位年参军学生、离休时任副地级的老干部电话中说,这是我看到的写喀什地区“文革”最真实最深刻的一本书。《我的一九六九》中,他在邻近木华里的一个公社当书记。一位北京青年打来电话使我愣愣地站了半晌。他说,你的书写得很好很真实,尤其是对我们北京哥儿们的同情写得很感人。但是,能不能不要在北京发行。我们回北京快三十年了,对孩子们一直说我们去新疆兵团是“为国守边、没有功劳有苦劳”,你的书中写我们“被枪杆子押送去的”“少管犯”,这确实是真实的历史,但我们对孩子们不能这么说、不想让孩子们知道我们经历的痛苦、屈辱、黑暗……这也许是“魔鬼的药酒”发散了。我震动了感动了拓荒者······ “司马迁”与《拓荒者》 兵团史志办太冷僻了。刚到这里朋友打电话问在干啥,接着问史志办是干啥的。答就是司马迁那个岗位,朋友立刻恍然大悟了。兵团历史研究把我从拓荒者变成殉道者。鲁迅称《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的最杰出的贡献是把历史当作人的活动来写,而人是有优点缺点的,他居然敢写刘邦年轻时的无赖行径,写韩信的胯下之辱,这些都被后世的封建皇朝否定了,而被千百年来的文学家继承发扬了。我自觉地把兵团历史看成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活动,在浩瀚的史料中把星星点点的人的情感挖掘出来。而且,我站在兵团历史的高度回望我的个人经历,就有了新的感悟:你可以一辈子不登高山,但你心中不能没有一座高山。这座高山是一种信仰,一种精神,一种追求。我穿越时空,看到陶峙岳年再次入疆任国民党警备司令,在飞机上心中默念唐边塞诗;进疆后在错综复杂的激烈矛盾中力挽狂澜选择和平起义;我把陶将军的历史选择看成是他的人生博弈,成文《生死博弈在险峰》;我在老红军老八路的回忆录中,选了王震的五个小故事:修和平渠拉石头,修十八团渠修改渠线,建设石河子路边捡到一块砖揣在皮大衣里等,写了《迅雷发叱咤,细微见精神》;我把《张仲瀚的生活情趣》从吃喝玩乐四个方面延伸开去,突出了一个高级领导的文化素质对兵团事业的重要影响。在深入团场收集史料的过程中,我一次次被许多人的悲欢离合,牺牲奉献所感动。我在孙龙珍烈士墓前握拳举手,高诵入党誓词;在边境农场凝望兵团人与苏军“扛膀子”拔铁丝网的山口;在塔里木河畔凭吊上海知青的陵墓;在北屯团紧紧攥一把兵团人战洪水,堵决口,保卫的国土;每一个边境农场的人的经历都是一部可歌可泣的故事。我们不渲染苦难,更不歌颂苦难,但我们兵团人一次次在苦难中崛起,一次次牺牲奉献而且无怨无悔。一个三五九旅老战士在和田荒原干了一辈子,在临终弥留之际已经不能回答亲人的呼唤,但是问你是哪个部队的,他立即用最后的一口气准确地说出了部队番号。一个西路军的少年红军被俘,九死一生,辗转进疆参加了九二五起义,“文革”中被打成“大叛徒走资派”进了“牛棚”,在危重病人抢救室他一次次鲜血,在团场小儿麻疹流行时,他夜以继日抢救孩子,七八十列病儿无一死亡。感人至甚的故事太多了,我选了二十个故事组成了纪实散文集《拓荒者》。只有一个愿望:守望兵团人的精神家园。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追求金钱名利,物欲横流;兵团文化被社会潮流边缘化,甚至被贬低否定。但是,我们非常清醒非常坚定,在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滚滚潮流中,我们即使是一朵浪花稍纵即逝也要闪烁太阳的光辉,即使是一脉拍岸的潮头也要“手把红旗旗不湿”,即使是一响水激的涛声也要喊“站起了我是界碑,躺下来我是绿洲!”《拓荒者》出版后,我念诵着这句诗:兵团人是被诗歌牵着走的骆驼。诗歌是理想追求,骆驼是坚韧顽强。只要沙漠在,拓荒不会停止。走吧,像殉道者坚定地从一个绿洲走向新的绿洲······ 相关链接: 陈新元《我的求学之路》 陈新元《苏州散记》 陈新元《景山听歌》 陈新元《西子美与大漠美》 陈新元《东北人、东北松》 陈新元《我与恰玛古》 陈新元《哈密“左公柳”诗考》 陈新元《阿克苏寻玉记》 陈新元《故城蹄声》 陈新元《方神遥祭》 陈新元《古老的“巨洼孜”》 作者简介 陈平,网名陈新元,新元。年元旦生于喀什伽师县,父亲为国民党四十二师骑兵团连长,参加九二五起义。本人年参加工作,在农一师,三师工作33年。当农工,测工,教师,新闻干事,宣传处长,文联主席等。发表新闻,文学作品五十余万字。年调兵团史志办处长,兵团民协主席。参与多部师,团志,老干回忆录审读工作。年退休。曾参与中央电视台播出纪录片《奠基西部》巜兵出南泥湾》巜王恩茂》等策划,接受采访工作。现居乌市。个人专著散文集《走过喀什》兵团史专著《拓荒者》纪实文学《大漠足音》《昆仑岁月》等。 《丝路听雪》编委 顾问:熊红久赵光鸣孤岛赵英秦一 主编:心悦 副主编:潭影白梅 编辑:西北望隆回四海纵横 主播:温晓萍王丽楠贾安合马踏飞燕 周静墨志李新泉轻言细语、杨佳妮蝶儿 《丝路听雪》投稿须知 1、本平台只刊原创作品,题材不限(诗词、散文、小说、篆刻、字画等)。现代诗歌3首以上,古诗词5首以上。散文千字左右,不限篇数。来稿请附字以内个人简介及本人高清照片3张。 2、投稿邮箱 qq.白癜风早期症状能彻底治愈好吗北京治疗白癜风的医院在哪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tumushukezx.com/tmskshj/2269.html |
当前位置: 图木舒克市 >陈新元拓荒与殉道我的文学心灵史
时间:2018/5/31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各个城市名片组成了新疆这个神奇的地方
- 下一篇文章: 经农三师多个团部抵阿瓦提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